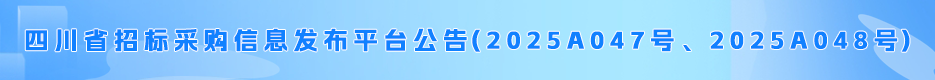■ 裴育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同时,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可见,政府预算是我国国家治理实现现代化的有效工具。
从新中国成立至今,政府预算可分为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从1949年到1978年,为计划经济时期的政府预算制度构建阶段。其特点是:在预算形式上采用单一预算,预算编制原则上贯彻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原则,长期沿用基数法编制预算,预算编制程序采用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逐级汇总的方法,预算管理总体上比较粗放,预算编制透明度不高,存在着非程序化和非规范化等问题。第二阶段,从1979年到1998年,为体制转轨时期的政府预算制度改革探索阶段。主要就统一预算编制方法、复式预算改革、预算编制程序等问题进行了尝试,但各地普遍存在预算约束软化问题。第三阶段,从1999年开始至今,为公共财政建设时期的政府预算制度改革深化阶段。主要表现为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收支两条线、政府收支分类等改革,并强化预算编制的科学化与精细化。
1999年以来的预算改革实质上是通过重构预算过程来进行权力结构重构和改变预算决策行为。一方面,部门预算改革、国库集中收付改革和政府采购就是要重构财政部门和各个部门之间的权力结构,将财政部门建成一个真正的核心预算机构,由它来集中资源配置的权力,对各个部门进行预算控制;通过国库体制改革使得财政部门能够对各个部门的支出行为施加外部控制。同时,部门预算改革使得政府提交给人民代表大会的预算报告包括了比原来更加详细的预算信息,将有助于人民代表大会对政府预算从外部进行控制。另一方面,这些改革都通过规范预算过程参与者的预算行为来实现预期的预算结果。
政府预算在本质上是以国家为主体的财政收支系统。预算权力是国家公共权力的核心之一,也是国家利益矛盾最集中的地方。预算分权就是要将预算权力在立法机关、政府、政府财政职能部门及内部各组织机构、独立审计机关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进而形成一个相互制约的运作体系。如建立预算的编制、执行、监督三者相互分离的制度,形成三套互相制约的机构;建立资金的使用权、支付权、审核权相互分离的制度;实行财政集中支付和政府采购制度;建立一套独立于政府、直接对人大负责的审计监督系统,并独立行使监督权。根据国家治理的需要,我国预算改革的重点是建立控制取向的公共预算制度,尤其需要设计各种在政府内部加强控制的技术工具;在借鉴国外经验时,尤其需要提醒的是,我们不能简单照搬他国做法,更需要看其处在与我国相同预算发展阶段时在做什么,看其面临与我们相同问题时是怎么解决的;任何缺乏历史感的预算改革不仅不能成功,甚至可能误导预算改革。
我国国家治理的转型与现代化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选择。政府预算改革既是国家治理转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推动国家治理转型的基础和保障。国家治理转型过程的社会矛盾越来越聚集在财政领域,形成巨大的财政压力,一方面要求继续发展经济、增加国家财力,另一方面要求更合理、更有效地发挥财政功能,既要提高国有资产的盈利和增值能力,又要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突出财政的公共性属性,保证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实现中国梦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如何缓解巨大的财政压力以及处理社会矛盾,是考验党的执政能力和国家治理能力的重大课题。只有抓住政府预算改革和行政体制这两个关键,并真正用科学发展观来指导这场改革,真抓实干,才能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以及现代化。(作者系南京审计学院副院长)
来源:中国政府采购报